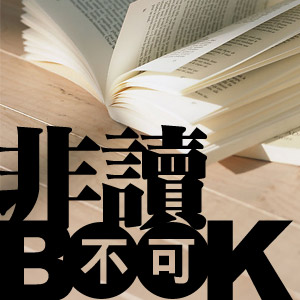核子時代即將結束。現在是軟體的時代,未來的決定性戰爭將由人工智慧驅動,發展進程和過去的武器完全不同,而且速度更快。硬體和軟體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根本性的逆轉。
在二十世紀,我們開發軟體主要是為了維護和服務硬體的需求。從飛行控制到導彈航空電子設備,從燃料系統到裝甲運兵車,都仰賴軟體的協助運作。
然而,隨著人工智慧興起,以及在戰場上使用大型語言模型來處理資料並提出針對性的建議,軟體和硬體的關係正在改變。如今掌舵的是軟體,硬體——例如在歐洲和其他戰場的無人機——則越發成為執行人工智慧決策的工具。
AI武器時代的缺席投資:落後的國防思維
無人機群能瞄準並殲滅對手,成本只占常規武器的一小部分。然而,我們對這類技術以及相關必要軟體系統的投資仍遠遠不足。美國政府主要還是在發展傳統的基礎設施,例如飛機、軍艦、坦克和導彈,上個世紀這些武器可以為我們在戰場上帶來優勢,但這個世紀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它們不再是重心所在。
美國國防部要求政府在2024年為人工智慧提供總計18億美元的經費,僅占國防總預算8,660億美元的0.2%,也就是1%的五分之一。如果一個國家對於自己使用武力的道德標準遠高於對手,那麼就算該國的科技實力與敵方持平,仍不足以確保優勢。如果受道德約束的社會掌握了武裝系統,強調武力必須謹慎使用,那麼這個社會必須比不惜濫殺無辜的對手更加強大,武裝系統才能真正發揮有效的嚇阻作用。
矽谷的道德困境:拒絕為國防服務的一代
我們的挑戰在於,矽谷頂尖的工程人才雖然有能力開發出本世紀最具嚇阻能力的人工智慧系統,他們卻對為美軍工作一事猶豫不決。整整一個世代的軟體工程師有能力打造出下一代的人工智慧武器,卻拒絕參與國家計劃,對混亂的地緣政治和道德的錯綜複雜毫無興趣。
近年來,雖然有一小群支持國防工作的人才出現,但絕大多數的資金和人才仍以消費市場為主。科技圈出於本能爭相為開發影片分享程式、社群媒體平台、廣告演算法和線上購物網站募資。他們毫不遲疑追蹤我們在網路上的一舉一動,將這些行為變現,深深滲進我們的生活當中。
然而,同樣也是這些工程師,以及他們打造出來的矽谷巨擘,每每談到軍方合作就躊躇不決。當然,諷刺的是,矽谷那些反對和軍方合作的人,他們享受的自由與和平,其實來自美軍可信的武力威懾。
我們的風險在於,這一代的人對國家的幻滅與對集體防禦的冷漠,導致無論是人才還是財務上的龐大資源,都被理所當然地用於滿足資本主義善變的消費文化。我們喪失了文化抱負,不斷降低對科技產業的要求,也不再期待科技業開發出效益持久且對公眾有集體價值的產品。我們任憑市場的短期需求壓過一切,把太多控制權讓給隨心所欲的市場。
在耶魯大學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教授文化人類學的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2012 年在《異見者》(Baffler)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網路是個了不起的創新,但我們說的頂多就是個超高速且全球皆可造訪的圖書館、郵局和郵購目錄的集合。」他希望我們可以做得更多,許多人也認同這點。
AI企業的界線?OpenAI與軍事應用之爭
2022年11月,OpenAI第一次公開自家的人工智慧介面,它們已投入幾十億美元開發ChatGPT等大型語言模型。然而,OpenAI的政策明確禁止把這些技術用於「軍事與戰爭」目的。這個規定是一大讓步,為的是迎合那些不願與保家衛國的軍人有任何關係的人。
2024 年初,OpenAI改弦易轍,取消了對軍事應用的全面禁令。隨後,抗議人士馬上聚集在公司執行長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位於舊金山的辦公室外,要求OpenAI「終止和五角大廈的合作,拒絕所有軍事客戶」。開發ChatGPT這種語言模型的工程師促進了計算智慧解決問題的重大突破,他們樂於奉獻自己的技術給消費性企業,但當美國陸軍和海軍請他們開發更高效的軟體時,他們卻顯得遲疑不決。
這類抗議和公眾憤怒的威脅在於,它會影響整個科技業的高層與投資人的決策本能,許多人已經習慣系統性地迴避任何可能會引發爭議或不滿的議題。這種迴避的代價極大,加上整個產業幾乎完全屈從市場隨心所欲的需求,由市場決定應該打造什麼,而非能夠打造什麼。
大創意荒:科技雄心的萎縮
2018年,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edia Lab)的共同創辦人尼可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設計與科學》(Journal of Design and Science)期刊發表過一篇叫做〈大創意荒〉(Big Idea Famine)的文章。文中指出:「如今有無數的新創公司正努力讓我們可以更輕鬆地洗衣服、送餐,或用新的應用程式來自娛。」他補充說,挑戰在於「為了迎合投資人的期待,新創公司往往把新技術、科學與工程發現和發明大材小用。」許多企業家和極有天分的工程師只是把難題擱在一旁。
經濟學家羅伯.戈登(Robert J. Gordon)認為,在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裡,美國社會的生產力顯著下降。正如戈登所言,自1970年以來這幾十年,科技發展「大多出現在娛樂、通訊、資訊收集與處理等狹隘領域」,而「人類在意的其他面向,例如食衣住行、健康以及居家外出的工作條件則進展緩慢」。
馬斯克是異端還是英雄?
不過,科技業泯滅雄心的普遍情況也有例外。舉例來說,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創辦了電動車公司特斯拉(Tesla)和太空公司 SpaceX,當國家和政府裹足不前,這些公司填補了明顯的創新空白。在上一個時代,開發可靠的內燃機替代技術,並將火箭送上太空的挑戰,理應屬於由政府主導的領域。這些挑戰需要龐大的資源,然而,願意冒著資本或個人名譽的風險嘗試解決這些問題的人太少了。當今文化幾乎都在嘲笑馬斯克對宏大願景的追求,彷彿億萬富翁就該安分守己,專心充實自己的人生,偶爾成為八卦專欄的話題即可。
2023 年,《紐約客》(NewYorker)雜誌刊了一篇描述馬斯克的文章,文中指出,世上要是少了幾個「打造外星星球的超級富豪」會比較好,還譴責馬斯克「似乎和人類本身漸行漸遠」。*2015 年有一本關於馬斯克的傳記寫道,多年來,許多人深信 SpaceX 研發可重複使用的火箭根本「徒勞無功」,並認為馬斯克「完全在浪費時間」。無論是出於好奇還是興趣,世人基本上都否定馬斯克創造出來的東西之價值,不然就是用一層輕蔑的面紗掩藏起來。
諷刺的是,許多極力反對資本主義過度發展的人,往往第一個跳出來抨擊那些大膽嘗試、打造市場無法提供的東西的人。我們需要的是更遠大的雄心和嚴肅的態度。
反抗溫和的墮落:奪回科技與文明的意義
舉例來說,iPhone 是不是人類文明最偉大的創造性成就?物品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如今那些東西也有可能限制並束縛我們的可能性。帕蘭泰爾的共同創辦人彼得.提爾(Peter Thiel)2011 年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衡量自身與評估人類進步的標準,應該是阿波羅太空計劃這種激進且重大的突破,而不是循序漸進改善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功能。
新一代崛起的創業家口口聲聲說自己冒險進取,然而一談到積極介入公共關係或重大的社會挑戰,他們往往戒慎恐懼。如果可以打造應用程式,何必冒險捲入地緣政治的道德泥淖、引發爭議呢?
他們的確打造出應用程式。社群媒體帝國在美國各地攻城掠地,有系統地操控人對地位與認同的渴望並把渴望變現,鎖定並洗腦年輕人尋求同儕的好感和認同,卻因此移轉了整個文明過多的心力和資源。
2022 年,YouTube 靠著針對3,140 萬名十二歲以下兒童的廣告獲利 9 億 5,900 萬美元。Instagram 在一年內也從這個年齡層的觀眾賺進 8 億零 100 萬美元。我們必須起身反抗,對於錯誤引導文化和資本的作為發出怒吼。「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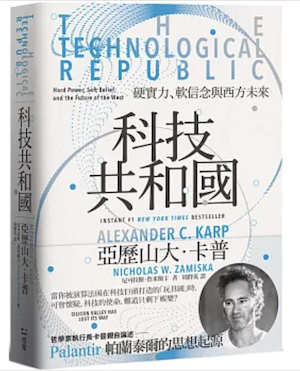
《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念與西方未來——Palantir 帕蘭泰爾的思想起源》
作者: 亞歷山大・卡普( Alexander C. Karp)、尼可拉斯・詹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
譯者:周群英
出版社:感電出版
出版日期:2025/10/1
作者簡介
亞歷山大・卡普(Alexander C. Karp)
帕蘭泰爾科技公司的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該公司於2003年在加州帕羅奧圖成立,專門開發軟體給美國及盟國的國防和情報機構使用,也供商業部門的企業使用。卡普畢業於哈弗福德學院與史丹佛大學法學院,並於德國法蘭克福的歌德大學取得社會理論博士學位。
尼可拉斯・詹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
任職於帕蘭泰爾科技公司執行長辦公室,擔任企業事務主管與法律顧問。他同時也是帕蘭泰爾基金會國防政策與國際事務董事會成員。在紐約市出生的詹米斯卡,畢業於耶魯大學與耶魯法學院。
責任編輯:林易萱